平冤筆記
冤獄平反涉及司法實務、科學鑑識、法醫學等各項專業領域,我們舉辦年度論壇,與各領域專家學者交流經驗;並與全國各地律師公會合作,進行教育訓練;舉辦各項講座、研討會、讀書會,期待更多人認識冤案的成因,投注心力,一同平冤。
本頁面收錄平冤過往舉辦各式活動、演講側記,保留相關專業知識與討論,也邀請大家從不同的角色、領域與專業,一起理解冤案。
依時序瀏覽

【圓桌論壇側記|112年憲判字第 6 號憲法判決評論】
平冤筆記, 年度論壇
記錄|高珮瓊
編輯|王季庭、柯昀青
本場次以聚焦「同案不同判」的112年憲判字第6號為核心,期盼開啟院方、辯方與學界的深度交流。我們邀請到了許玉秀前大法官為主持人,並由蕭奕弘律師報告,李念祖教授、李榮耕教授、蔡旻穎法官進行與談。
蕭奕弘律師在介紹我國軍審制度的演進後,首先說明此次憲法判決的爭點──原因案件中的兩名被告,分別走上軍事和普通兩種審判體系,結果一人被判有罪、另一人獲判無罪。原因案件的律師指出,相較於普通法院,軍事審判法院上命下從、審判不獨立,且依軍事審判法第181條第5項規定,被告沒辦法以「事實認定錯誤」為由上訴,侵害人民受憲法保障的平等、人身自由和訴訟權利。
獨立再審事由:民、刑事事實認定歧異的適用可能?
蕭奕弘律師說明,在這份憲法法庭判決中,大法官雖然認定軍事審判法合憲,但基於「在主要證據相同下,客觀事實只有一個,不可能有罪無罪兩者併立」的思考,另為受判決人開啟再審大門,也就是指明軍事、普通法院認定事實歧異的情形,可以作為一個獨立於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各款的聲請再審事由。
蕭律師認為,這彰顯了大法官對於「刑事法院會否開啟再審」及「軍事審判」欠缺雙重信心,才會逸脫刑事訴訟法第420條,增設獨立的再審事由,卻又限縮在軍事、普通法院不一致的本案才有適用。蕭律師接著以「陳敬鎧案」為例,指出該案中刑事判決1詐盲確定,但民事部分開啟再審後勝訴2,認定沒有詐領保險金,這樣是否可以提起刑事再審?由此帶領大家思考:獨立再審事由的範圍,有無擴張適用於類似案例的可能?
1詳參臺灣高等法院…

【圓桌論壇側記|林金貴的平反之路】
平冤筆記, 年度論壇
記錄|陳宣予
編輯|韋昱安
林金貴的案件在2023年1月11日無罪確定,成為平冤第14起平反案件。自林金貴2007年捲入冤案,至2023年平反成功,期間經歷了再審駁回、再次有罪等種種挑戰,可以說是清白得來不易。因此,本場圓桌論壇以「林金貴的平反之路」為題,邀請到林國泰律師擔任主持,和擔任義務律師團參與救援的陳偉仁律師、鄭植元律師、蔡晴羽律師以及羅士翔執行長進行與談,從不同角度探詢林金貴一案的救援過程。
羅士翔執行長:犯罪現場電光火石,行為人的五官不容易清楚記憶,而當警方有刻意暗示或誘導性的安排,指認就容易出錯。
在平冤過去的案件中,許哲偉、吳明峰、張振忠的案子都曾涉及瑕疵指認,而平冤在救援林金貴時,也在指認證據上發現許多問題。羅士翔執行長說道:「判決書上有三位證人指認,指證歷歷,平冤協會在調查的時候就留意到,既然三位都與阿貴毫無仇恨、毫無糾紛,有可能故意指錯嗎?」
平冤在案件的指認紀錄表上發現了兩大疑點。第一,指認表上有四張照片,其中三人是臉部清楚的大頭照,而另一人──也就是林金貴──則是中景的半身照。林金貴的左手背在身後,似乎是銬在欄杆上,跟另外三人明顯不同。第二,指認表上有三個指印,分別是三位證人分別蓋印。但指認牽涉的是個人的主觀認知,三位證人接續指認,可能前後汙染,並不符合指認程序。而且三位證人中,潘先生和邱先生是現場的目擊證人,但另一位林女士,實際上並不在犯罪現場,也就是她沒有看到行為人,與犯罪現場是沒有關聯的,卻也來指認,令人起疑。
平冤在觀察到這些疑點後,曾經去拷貝卷內的影音資料,發現那位林姓證人在警詢錄音時,有一段對話並沒有記錄在筆錄中。錄音內,警察問林女士:「你有願意指認殺人犯的嫌疑人嗎?」,林女士答道:「都已經聊到這裡了。」警察回覆:「不會啦,你在煩惱什麼,我保護你安全。」從這段對話,讓人覺察林女士似乎是為了配合警方而做的指認。
除此之外,平冤還在卷內發現了一個紀錄,林女士在指認林金貴之前曾表示,她的前夫與監視器拍到的涉案對象相似。但這份資料的來源是一個警察局的分工紀錄表,類似於警察間的工作報告,此對話過程並沒有做成筆錄,也沒有錄音可供佐證。但至少能夠從此得知,林女士曾經指認他人,他對林金貴並非如此指證歷歷。
而另外兩位證人潘先生和邱先生,曾經在現場跟嫌疑人有一段追逐的過程。兩人描述,當時在追逐幾個巷弄後,嫌疑人亮槍,兩人便停下不敢輕舉妄動。根據美國的研究,犯罪現場的指認會產生「凶器聚集效應」,現場的人會因為恐懼而將目光聚集在凶器,而非行為人的五官,因此兩位證人是否能清楚看到、記得嫌疑人的特徵,不免要先打上一個問號。再者,這份筆錄是在案發後五個月所做的資料,為何警方會在經過五個月後還能找到兩人進行指認?可以推測出,在案發後,警察就有對兩人作了相關的談話紀錄留下資訊,但這些資料同樣沒有出現在卷中。
總結而言,有罪判決引用了這三個證人的證詞,但事實上,林女士不再現場,邱先生和潘先生可能因為凶器聚集效應無法掌握臉部資訊,指認表更在程序上有誘導性的安排,整個指認過程疑點重重。而除了這三個證人外,卷內還有一位秘密證人A1,他在案發後十個月指認林金貴為嫌犯。這位A1在經過資料的比對後,推測出他是在案發後一個月就曾進行過指認的陳姓小朋友,而他當初指認的是一位已排除嫌疑的郭姓男子,也就是說,這位祕密證人A1曾經誤指他人。
「這是對林金貴有利的資料,卻沒有完整的呈現在卷內。」
平冤協會在2014年翻譯了《路人變被告:走鐘的刑事司法程序》一書後,便留意到美國最嚴重的冤案成因正是指認的瑕疵。案發現場本來就電光火石不容易記憶,若指認程序中還參雜警方誘導性的安排,指認就有可能出錯。羅士翔執行長強調:「因為證人與被告常常是毫無關聯的,沒有利害關係的考量,所以(證詞)在法庭上會很容易被採信,因此指認的證據是我們需要更嚴謹、更審慎地去面對的。」
陳偉仁律師:明明都是一樣的證據,法官有罪給一套理由,無罪給一套理由,法官判決的寫作技巧可以跟無罪推定原則相牴觸嗎?
陳偉仁律師與林金貴案件的淵源,源自過去羅秉成律師在台大開設的冤案救援實務課程,在課堂上,羅律師請同學們提出三個問題,分別是:卷有什麼問題、案情有什麼問題、確定判決本身有什麼問題。而這三個問題也是陳偉仁律師今天的討論重點──卷內的不在場證明、行兇的動機和測謊證據的採用。
首先,陳偉仁律師介紹了在林金貴案中的測謊證據採用。原確定有罪判決的證據結構並未採用通過測謊這個對林金貴有利的證據,而法院提供的理由是,測謊距離案發時隔六月,且測謊不能作為有無犯罪事實的唯一證據,參酌其他事證後決定不採。而在認定無罪的版本內,則是以林金貴堅持否認,並測謊通過為理由,處理測謊這個證據。陳偉仁律師說,關於測謊的確有一些制度上的問題,測謊是否能當作有罪判決的證據是個爭議點,但如當初對林金貴實施測謊鑑定的羅警官所說,雖然測謊可能無法總是符合刑事鑑識的「再現性」,但它既然擁有一定的科學技術和理論,那在無罪推定的基礎下,是否能夠在冤案救援時輔證無辜者的清白,便是值得討論的方向。
接下來談到案件中的行兇動機交代。在有罪判決內,因為無法交代,所以判決只寫了「不明原因」;在無罪判決內,則以林金貴自始至終堅稱否認行兇,否認犯行態度始終如一,因此無法想像林金貴的動機,參酌其他事證後判林金貴無罪。同樣無法得知動機,在不同判決中卻有著不同結果。
最後則是林金貴的不在場證明。此案的案發地點在鳳山,案發時間為晚上9點35分,而林金貴在1小時5分後,有一則通聯記錄,基地台顯示人在台南佳里。在有罪的判決內,法官採用警員實測的時間,說明兩地在一小時內能夠到達。而無罪判決的說法則是著重在不清楚行車路線,也不清楚交通工具如何取得為由,認為林金貴應非犯案的兇手。
「我當時的疑問是,明明都是一樣的那些證據,法官有罪的給一套理由,無罪的給一套理由,法官的判決寫作技巧可以跟無罪推定原則相牴觸嗎?」在說明三項證據在不同判決中的不同結果後,陳偉仁律師以此作為結語,將這些疑問留給大家思考。
鄭植元律師:沒有坐過冤牢,不能體會刑事訴訟法對於證據要求的重要性
鄭植元律師接續說明再審讓林金貴三審發回的關鍵之一:獄中線民林慶楨、歐陽榕供述的疑點。
鄭植元律師回憶到,那時再更一審後又被宣判有罪時,背負的壓力仍然歷歷在目。接著,他針對當時的兩位不利證人:林慶楨和歐陽榕,仔細地跟與會觀眾分析他們證詞的不合理之處,並強調完善的刑事訴訟程序的重要性。
林金貴案中,沒有兇器、缺乏動機,而湊巧出現的這兩位證人,完整了檢方的故事。鄭植元律師解釋,在警詢中或偵查中,筆錄不可能一字不漏記下來,但是重點應該要節錄。證人林慶楨說林金貴曾經有亮槍給他看,然而當律師團聆聽這份筆錄的錄音檔時,可以發現林慶楨的說詞與筆錄有很大出入,林慶楨所描述的那位「亮槍之人」,與林金貴的特徵並不相符,在警詢錄音中,警方還對林慶楨有疑似交換條件之利誘情形,林慶楨甚至明言要看員警的表現才在筆錄上簽名。
另一名證人歐陽榕則是表示在獄中聽過林金貴自承有犯案,而且充滿細節,但鳳山分局並未錄音,無從檢證歐陽榕如何製作筆錄,鄭植元律師不禁對於他完整如起訴書事實一樣詳細的證詞抱持懷疑,果不其然在交互詰問時,歐陽榕說只是聽聞其他獄友討論,傳喚另外兩位獄友亦證實林金貴並無坦承犯案,歐陽榕的證詞可說是破綻百出,最終不被法院採納。
最後,鄭律師再次強調:「沒有坐過冤牢,不能體會刑事訴訟法對於證據要求的重要性」,每個證據都有可能影響當事人的一生,需要各方更重視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
蔡晴羽律師:感謝林金貴的堅持,終於走向清白
本場最後與談人蔡晴羽律師則分享在林金貴的平反之路上新證據的發現,從她與本案的初遇,細談其中閱卷、尋找疑點和破點的關鍵,直抒從還在路上的冤案走到被平反的冤案的甘苦談。
蔡晴羽律師回憶到,第一次在台大冤罪救援實務課程中見到林金貴,只是一疊卷宗,這是她第一次研究判決確定案件。她提到在當事人喊冤後,理卷上的關鍵應有:「疑點、弱點、破點」以及證據構造分析的再造。
當時班上的同學在林金貴的案子中找到了許多疑點,例如沒有毛髮、指紋不符、林金貴通過測謊、沒有凶槍、弔詭的指認過程、動機不明。確認案件有疑後,便開始尋找破點。當時再審需要使用「已存在但未及調查斟酌之證據」,面對嚴苛的再審舊判例,羅秉成律師提出了一個破點:不在場證明。卷中有一張台南佳里到案發現場的地圖,已存在卷宗且未被證據提示,符合當時的再審規定。然而,第一次的再審卻被高雄高分院的法官以簡單的數學計算駁回。
駁回後,大家重啟相關證據的調查,將有疑點的部分重新檢視,盼有新轉機。律團會議上,參與救援的周慶昌同學提出是否能確認林金貴案發前後頭髮長度的可能,在阿貴姊姊的翻箱倒櫃下,真的找出林金貴在案發兩個月前辦身分證所用的證件照,為案件帶來一線曙光。
在歷經第一次再審被駁回後,律團經過更嚴謹的調查,第二度提起再審。高分院當時也做了許多調查,包括以林金貴頭髮作實驗,而收到醫院回函說明林金貴的頭髮生長速度與正常人無異,與刑事警察局函詢光碟的真實性,其回覆也表示僅有少許修改。蔡晴羽律師回憶到,當時大家心中對於再審的開啟都很期待,沒想到高分院卻以光碟拍照時間與燒錄時間相隔一天,無從證明拍照時間為由,且頭髮生長速度與9年前可能不同為由駁回。憤怒後,蔡晴羽律師只能調適心情,默默地寫抗告理由,所幸法院最終還是開門,開啟再審。
蔡晴羽律師總結,這一路上走的並不平穩,也曾經被改判有罪,幸好有林金貴的堅持,這個案子終於走向清白。
林金貴:自己的冤案(自己)救!
講座尾聲,林金貴親自上台分享自己的心路歷程。
林金貴說,自己從來沒有想過會去研究法律,「有時候要靠律師,但有時候要靠自己,因為自己才是最了解案子的人」林金貴還分享了自己在監時研讀六法全書、寫信時為了寫出工整的字而做的努力1。他也在台上感謝姊姊、姐夫、平冤的同仁及平反者陳龍綺的付出,謝謝他們讓自己今天能站在這裡跟大家說話。最後,林金貴用他在平冤路上的座右銘做結:「我一個只讀過小學的人為什麼會想要去念法律呢?因為,自己的冤案要自己救。」
1詳細可參考冤冤相報no.149…

【圓桌論壇側記|「意圖販賣而持有 」之事實認定】
平冤筆記, 年度論壇
記錄|劉書瑋
編輯|沈文莉、韋昱安
本場…

【圓桌論壇側記|司法詢問員制度在偵查階段之運用】
平冤筆記, 年度論壇
記錄|鍾咏倪
編輯|王季庭、柯昀青
2023平冤論壇第二天的下半場,我們邀請尤美女律師主持,由陽明交大科法金孟華教授分享司法詢問員制度在偵查階段的可能運用,並邀請台大心理系趙儀珊副教授、台南地檢署李駿逸主任檢察官、以及現代婦女基金會王秋嵐研究員進行與談。金孟華老師開場即明確表示,本場圓桌論壇與當日上半場的主題演講《供述鑑定的鑑定方法》密切相關,歡迎與會者和上半場的講者趙儀珊教授接續討論。
金孟華副教授:司法詢問員是中性的技術,不是為服務訴訟中的任何一方而生。
金教授提及「司法詢問制度(forensic…

【主題演講側記|關於供述鑑定之鑑定方法】
平冤筆記, 年度論壇
記錄|曾閔
編輯|謝佳恩、韋昱安
2023平冤論壇次日,我們邀請到多次擔任法院鑑定人的趙儀珊教授來向與會者分享關於供述鑑定之鑑定方法。一開始,趙老師先向聽眾們說明她針對「警詢筆錄」多年的研究經歷,因為對於法院而言,此為是否有鑑定人資格的重要判斷依據,將直接影響到是否要讓其鑑定該案之供述證據。
供述鑑定的評估
在做供述鑑定或評估自白者的鑑定時,「被詢問者可能在什麼樣的因素影響下,做出這個陳述?」是鑑定人所關心的,故會針對被鑑定者的每一句進行評估與分析。實務上,根據法院的需求與刑事訴訟程序的階段不同,主要分為偵查階段、審理階段兩個面向進行供述鑑定的評估。
在偵查階段,鑑定人多以專家鑑定人或協助司法詢問之專業人員身分,針對「證人、嫌疑人提供的證詞或自白」、「警詢或偵訊的品質」等進行評估。針對前者,必須評估受鑑定人說了什麼、在什麼樣的狀況下以什麼身分說的,接著從受鑑定人的行為與反應綜合評估,最後做出鑑定意見;後者則是於警察、檢察官進行訊問時,提供「是否有暗示性、誘導性訊問」之意見。
當案件進入一審判決前、判刑前或二審等審理階段時,鑑定人轉為鑑定「被質疑之事項」,例如針對某方證詞、自白可信度與警詢、檢察官偵訊品質等提供鑑定意見。講到這裡,趙老師特別提醒到,鑑定人只能針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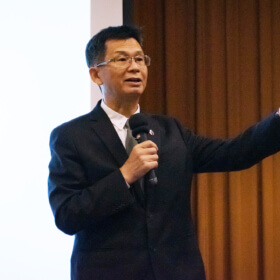
【主題演講側記|發展標準在司法科學制度上的重要性】
平冤筆記, 年度論壇
記錄|林宥妤
編輯|林執安、韋昱安
經過第一場次Lynn…

2018平冤年度論壇|櫻井昌司主題演講講稿──「從冤案中起身-布川事件44年的真實」
平冤筆記2018年8月25日台灣冤獄平反協會年度論壇
譯者:許博鈞、林慈政、孫斌、李怡修
布川事件序幕
我是櫻井昌司,我親身經歷過一個冤案,這個案子在日本稱為「布川事件」。
今天非常感謝「台灣冤獄平反協會」的邀請,謹在此向協會的各位朋友,表達深深的謝意。另外,也非常謝謝今天在百忙中出席的各位來賓。
我對台灣的法律及司法制度不太了解,因此,以下所說的事情只會涉及我在日本親身經歷過的冤案,以及經歷後的一些想法、理解,還有,我現在的願望。不知道我今天的演講內容能不能達成這個大會的目標,但我接下來,我就談談我在獄中29年的生活,以及44年間持續努力平反冤案的經驗。請大家多多指教。
51年前,也就是1967年8月28日晚上,在日本茨城縣利根町一個叫做「布川」的地方,有一位62歲的獨居男性遭到殺害。因為房間內有被翻動的痕跡,警方以強盜殺人方向開始偵查。因為事件發生在叫做布川的這個地方,因此被稱為布川事件,我與杉山卓男先生,被當成這個事件了犯人。這就是這個事件發生的起始。
我跟杉山兩個人都住在利根町,當時分別是20歲、21歲的年輕人。我們都是被稱為不良少年的人,過著不怎麼光彩的生活。具體來說,杉山屬於毆打、恐嚇讓人把錢交出來的暴力份子。相對地,我則是低調地,趁人不注意時偷竊財物。因為類型不同,我們的關係其實也不怎麼好。
依照日本警察的偵查手段,會先懷疑一般人所說的「壞人」,以此為起點開始偵查。如果是現在,大概會先到處收集調查監視錄影,從中過濾出犯人。在51年前,除了在案發現場採取指紋等證據,尋找目擊者之外,同時也會鎖定有前科的人,或是有負面傳聞的人,聽說那個時代是這樣開始偵查。
布川事件中,從案發現場採取到的物證有「43個指紋.掌紋」、「8根頭髮及陰毛」。案發現場的目擊證人部分,有一個31歲的母親,以及她12歲的兒子,她們一前一後在數分鐘內從房子前面經過,分別目擊到兩位男性。一位站在房子前,另一位則是在廚房的出入口,與被害人談話。
警方以這兩位男性為犯人的方向開始偵查,據說也有人被逮捕偵訊,但始終找不到犯人,一直到了10月10日(譯者按:大約案發後40天),我因為涉嫌偷竊「朋友的褲子及皮帶」而被逮捕。從這個時候開始,冤案.布川事件正式拉開序幕。
我的虛偽自白
日本警察裡有一句話,叫做「沒有確證的確信。」也就是說,即使沒有證據,只要確信嫌疑人就是犯人,就要想辦法讓嫌疑人自白。這樣的傳統偵查手段,正是日本製造冤案的一個重要原因。
台灣已經施行了全程錄音錄影,因此,偵查過程中應該已經沒有人使用暴力手段了吧。相對地,日本在這方面的規範並不完善,僅有部分錄音錄影。對於沒有確證,只有確信而逮捕到案的被告,使用暴力式的偵訊,是被默許的。日本警方受到的訓練是,「既然已經逮捕,就要徹底給他好看,如果覺得自己抓錯人了,那就是輸了。因此,應該要把被告帶到偵訊室,跟被告比拼體力,想辦法讓他自白。」即使是現在,日本警察仍然使用這樣暴力式的偵查訊問手法。
差不多在兩年前,東京「杉並區」的一個國中生因為涉嫌偷東西,而遭受調查。在偵查過程中,警方威脅這個國中生:「你不承認我就不放你回去,讓你的一生到此結束!」因為這個過程有被錄音筆錄下來,經過媒體報導,大眾才知道這件事情。對於一個國中生的偵查,竟然會使用強暴手段,那麼,大家應該可以想像得到,對於成人的偵查又會是如何了。
51年前,取手(譯者按:地名,位於茨城縣內)的警察幹部對我說「你待在這裡的期間,我不會放任何人進來這個拘留所,你就慢慢住著吧」。之後,不是在偵訊室,而是在拘留所看守人員休息室內,從上午9點到午夜12點一直持續地逼問我。「趕快給我自白,我們有證據,有證人看到你跟杉山」。警官在「沒有確證,只有確信」的狀況下進行調查,因為這個警官相信,被逮捕的人就是犯人,因此,為了讓這個人「自白」,這個警官可以面不改色地說謊。
發生事件的晚上,我有不在場證明。當晚,我人不在發生事件的茨城縣,而是住在東京一個叫作「野方」的地方。我在我哥哥的公寓,也有到哥哥工作的酒吧喝酒。我跟警方說了不在場證明,但警方卻說「我們已經調查過了,你哥哥說你沒有去。不在場證明是假的。」畢竟那已經是距離案發超過44天的事情,警方的說法讓我以為自己記錯了。
逮捕後第5天,警方對我進行測謊,並告訴我「儀器顯示你剛才在說謊。你逃不掉的,趕快給我自白」。警方以這種方式逼我,最後,我在10月15日(譯者按:大約案發後50天)做了虛偽自白。
曾經有人跟我說「為什麼要自白?沒有做的話,應該繼續否認才對呀」。確實,如果冷靜地思考,的確是如此。但是,警局的拘留所內,連時鐘都沒有,是一個連時間感都會喪失的特殊環境。我不太清楚台灣的狀況,但在日本,警察一開始就會先叫被告把衣服脫光,確認有沒有偷藏凶器之類的。脫光被告的衣服褲子,一方是能夠命令對方脫光衣服褲子的人,另一方則是,縱然厭惡也無法抗拒,必須脫光衣服褲子的人。這兩種人所處的立場,有著懸殊的差距,這是很關鍵的。這個空間是,警官可以對被告為所欲為的密室。
請問今天的各位來賓,是否有哪一位有待在警局拘留所(譯者按:日本因看守所不足等問題,在警察局設有拘留所)的經驗?有這類經驗的話,可以舉手嗎?(譯者按:本句為譯者所加)(如果有來賓回答「我有這類經驗」,我希望能與該來賓對話,煩請幫我翻譯)
偵查,是一種精神層面的吵架。「就是你!」「才不是我!」是這樣的精神層面的對立。在3.3平方公尺的狹小空間內,每天超過12小時處於爭吵的狀態,是一種痛苦的精神折磨。
各位來賓當中,應該有人有與另一半吵架的經驗。也有人是與男朋友、女朋友吵架,或是在職場被上司或顧客責罵,而且是沒道理的責罵。請各位想像看看(譯者按:本句為譯者所加),把這類吵架或是責罵連續持續好幾天,這就是警察的偵訊。
持續的爭吵,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結束,而且每天都被毆打。如果是犯人,想到說出「是我做的」就要進監獄,那或許還可以忍著不承認;但是,無辜的人面對的是偵查過程中,精神及肉體上的痛苦,為了逃避這樣的痛苦,而做出虛偽自白。
在日本,有一個惡名昭彰的「代用監獄制度」,也就是不將被告關押在普通的「看守所」,反而是關押在警局內的「拘留所」,而且可以長達數日。依照法令,在起訴之前,可以長達23天。如果一個被告在「本案」之外(譯者按:本句為譯者所加),有「另案」的犯罪事實,那這個被告會被長期關押在警局內的拘留所,甚至可以說,已經沒有關押期限可言。無辜的人,沒有辦法忍受無止盡的偵查。
如果承認「是我做的」,偵查人員會問「那你怎麼做的,給我說清楚」,這時候無法回答「我不知道」,一定要說些什麼。但是,要做出虛偽自白是很簡單的。請大家想像一下,想像你已經承認,你就是布川事件的犯人。在承認之後,「我不知道」這種回答是說不通的。
案發時間是8月28日的晚上。當天白天超過30度,晚上也超過25度,這樣的溫度在日本稱為「真夏日、熱帶夜」。偵查人員問我:「被害人當時是穿著怎樣的衣服?長袖還是短袖?」大家想像得到答案嗎?接著,警官問我「是什麼顏色的衣服?」請問大家,知道答案嗎?可以想像到答案嗎?偵查人員聽到錯誤的回答,就會一直重複訊問,因此,任誰都可以說出答案。被害人好像是這樣死的,「穿著無衣領的白色襯衫,卡其色的工作褲」,要回答被害人的穿著,是出乎意料地簡單。
我之前住在事發地的那個小鎮。因此,關於這個事件,我有聽過一些傳聞,例如:被害人是在8張榻榻米的和室內,在壁櫥前遭到殺害。被害人嘴裡被塞了東西,且被白襯衫包覆起來。榻榻米遭到破壞,地板下的數百萬日幣被搶走。偵查人員手上有案發現場的示意圖,並以該示意圖訊問我,我則以之前聽過的傳聞作為線索,回答偵查人員的問題。要作出一份錯誤自白,出乎意料地簡單。
偵查人員說:「你殺了人,當時處於興奮狀態,因此,有些事情也不記得了吧。但是,多回答幾次,你就會想起來的。」
如此重複著一問一答,當偵查人員滿意我的回答時,就將我的答覆就記在筆記上。這樣的偵訊持續1、2個小時,任誰都可以做出煞有其事的自白。
雖然今日各個國家都是用電腦製作供述筆錄,但在51年前,則是由訊問者將問答內容寫在筆記上,再把筆記內容作成彷彿你如實招供一般的偵訊筆錄。
杉山在案件爆發的利根町是一個出了名的惡霸。雖然法院在9月下半就發出了逮捕令,但似乎因為他牽扯上地方的幫派鬥毆事件而逃到東京,導致比較晚抓到他。我在10/15被迫作出虛偽自白後就被逮捕,他也同樣地被迫做了虛偽的自白。因為上述兩份自白書,我和杉山被判處無期徒刑,其後的29年間,被迫在獄中度過。
員警偽造證據
對於因為他們毫無根據的確信而被迫自白的人,因為自身本來就是無辜,因此罪證不足,日本警察則用偽造證據來補強有罪的基礎。對我們受冤者而言,有組織性的偽造證據的日本警察,在世界上是相當異常的存在。接下來我們談談幾件警察偽造證據的案件。
在高知縣的仁淀川町,一輛校車和警用摩托車相撞,導致機動警察隊員死亡,這起案件被稱為高知機動警察事件。22名國三生與帶隊的3位老師所搭乘的巴士,在休息站用完午餐後,從停車場離開,要右轉至一條有中央分隔島的道路,正在等待的時候,被一輛警用摩托車以很快的速度撞進來。(譯者按:日本開車是右駕,想像時須注意。)在巴士後面跟著,駕駛自用車的校長,目擊了這場事故。坐在巴士上的22名學生、3名老師,坐在自用車上的校長和當時的駕駛片岡晴彥皆主張「巴士當時是停止狀態」,但法院卻認定巴士以時速6~10公里行駛而和警用摩托車相撞。
法院依據恰好行經對向車道的機動警察隊員所作的「巴士當時在移動」的證述,以及道路上留有約一公尺的巴士剎車痕跡,認為「身為專家的機動警察不可能會看錯,剎車痕是無可動搖的證據」,而為有罪判決。
關注冤獄平反計畫(innocence…

【法白 X 判決的艱難 講座】性犯罪在法律實務與現實的兩難
平冤筆記, 消息
「確認事實,永遠是判決最艱難之處。」
——《判決的艱難:兒童性侵的爭議與正義》
性侵案件時常缺乏明確的證據,只有雙方各執一詞,在充滿許多不確定的迷霧之中,我們要如何先將最容易被挑起的情緒放到一旁,冷靜、審慎看待性侵案件在判決時所面臨的艱難?
2023年7月28日,法白放大鏡系列演講「照入性別權力的背光面」最終場,邀請到《判決的艱難》的作者陳昭如老師,來向大眾分享「性犯罪在法律實務與現實的兩難」——司法審理究竟扮演什麼角色?我們期待的判決是否是被害人真正想要的正義?在認定性侵案有無發生的過程中,是否有可能出現無辜、卻被指控為加害人的被冤者?
書寫動機:「性侵冤案很像佛地魔,不能談、也不知道怎麼談。」
自2014年出版《沉默》一書,昭如老師已經接觸兒少性侵9年了。九年之中隨著其他書籍的出版,她對性侵案相關司法程序已有初步認識,但對於性侵冤案還是相當陌生。
「一般人可能不知道,性侵案件的審理有多難。」機緣巧合下,昭如老師看到了冤獄平反協會負責救援的許倍銘案所有的第一手資料,包含判決書、調查報告等。在艱澀的法律用語及報告書的縫隙中,她發現隱藏其中的重重疑點。由於性侵案發現場大多為僅有兩人的密室,不僅幾乎找不到證人,被害人也多因心理因素未在第一時間報案,使得科學證據的採集更加艱難,只能從雙方當事人的供述證據認定事實。
「出於對司法程序不夠理解或對法律的陌生,一般人對法庭抱持著過高的期待且往往無法好好審視性侵冤案,甚至認為談冤案會破壞被害人的權益。」因此,昭如老師用本書聚焦探討有關性侵案件審理時的司法有限性,期望引領不同領域的人們一窺司法程序的重重難關。
判決的艱難——「證據難,法官也難。」
不同於一般刑事案件,性侵案件的證據大多缺少證人,而必須依賴於科學證據的採集與雙方當事人的供述證據。然而司法判決講求客觀事實及法律認可的證據,假若證據不足便必須依無罪推定保護被告的權利,不能只憑被害人的供述而判處被告有罪。
「被害人的供述只是證據之一,你必須找尋其他的證據來佐證。」昭如老師說道。原告與被告為利益相衝突的兩造,且記憶往往隨著時間變動,雙方供述極有可能不相符且有認定上的疑慮。因此,除了供述證據外,更應以科學證據佐證、驗證,降低錯判的可能性。
然而,科學證據百分之百準確嗎?常見於性侵案件的科學證據有:
1…
依類別瀏覽
即將開放,敬請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