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利事件的衝擊-DNA鑑定及冤案救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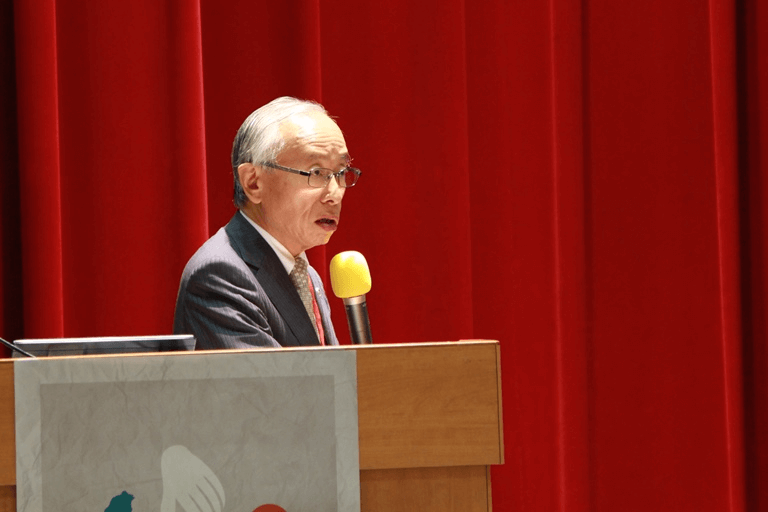
攝於冤罪救援與再審新制-台日冤罪救援行動交流暨冤獄平反協會2015年度論壇 (2015.8.22-8.23)
文/戴文欣,清華大學人社院,平冤實習生
足利事件為1990年5月12日在日本足利市發生的一名4歲女童遭姦殺棄屍於河濱的案件,事件過後半年警方逮捕了幼稚園司機菅家利和,並且靠著自白以及錯誤的DNA鑑定將他起訴,經歷三審皆被判決為有罪,直到2010年因正確的DNA鑑定證據而開啟再審,才還菅家先生清白。本次的平冤論壇邀請到此案的辯護律師佐藤博史先生來台,針對此事件與台灣的法律圈人士交流。
足利事件是日本第一起因為錯誤的DNA鑑定被判決有罪,又因為正確的DNA鑑定而判決無罪的案件。佐藤律師從1993年二審開始擔任被告菅家的辯護律師,一直到2010再審為止,一共經歷了17年。此次演說由「以DNA鑑定認定為無辜的意義」起頭,導入下一個部分「足利事件的衝擊」詳細說明足利事件,最後再以探討「藉由DNA鑑定進行冤罪救援的意義」作結。
以DNA鑑定認定為無辜的意義
DNA鑑定出現前就算法院判決無罪也不表示真的無辜,但若是以DNA鑑定而被判決為無罪的話即為真實無辜。若是被告自白的案件,在DNA鑑定出現前,即使法院判定自白不足採信,還是可以說這份自白是真實的,但若以DNA鑑定被認定為無罪,這份自白就是虛偽不實的。當然上述的DNA鑑定前提都是正確的鑑定,而非像日本科學警察研究所對菅家先生一開始做出的虛假鑑定。
而美國在累積DNA鑑定無罪案例後,開始對各項證據的採信程度進行修正,不只是自白、證人證詞等供述證據,對血型、毛髮、腳印、筆跡、測謊等所謂科學證據也有根本性修正。經DNA鑑定認定無辜,顯示出刑事上不被懷疑的證據其實不一定值得相信,此為刑事司法上的一場革命。
足利事件的衝擊
1990年5月12日足利事件發生後,警方根據犯人遺留精液測出的血型(B型分泌型)鎖定了足利市的某些成年男性,菅家先生為其中之一。警方發現菅家先生的租屋處有超過100部的成人電影以及充氣娃娃,懷疑他是欲求不滿的且喜歡女童的單身男性,因此從1990年11月之後開始跟監菅家先生。1991年6月,警方取得沾有菅家精液的衛生紙,委託科警研進行當時才剛引進日本的DNA鑑定,結果鑑定結果與犯人的MT118型基因座符合。在1991年12月1日早上,菅家先生被迫任意同行,也就是被強迫帶至警局詢問,並且在當晚自白犯罪,隔天即被令狀逮捕。他被逮捕並不是因為DNA鑑定,是因為他的自白。
DNA鑑定在當時才剛引進日本,還沒有像現在一樣精確的技術,而且在後來科警研的DNA鑑定被發現其實用的是被害女童的DNA,根本就是毫無作用的垃圾鑑定,但在當時,警方、法官、菅家原本的辯護律師和整個媒體都沉醉在DNA神話中,絲毫沒有人發現菅家做的自白是虛偽的,也沒有發現案件的怪異處。
縱然之後他不斷辯稱自己是清白的,寫給家人的信件也不斷強調此事,他的辯護律師卻也沒有相信他,只是把信件呈給法官就不管後續,明顯沒有盡到充分辯護的責任,他也算是菅家受冤的推手之一。DNA鑑定神話一直到2009年做出再鑑定結果後才崩壞,可見它對審判者的影響力根深蒂固,然而無限制的仰賴錯誤證據的結果,代價是他人的十七年生命自由。
菅家一案在證據上的疑點非常多,法院認定事實的故事情節也漏洞百出,甚至連現場的模擬都是依照警方所想要的故事而隨機做出來的,但會有這些審判過程和後續發展都是從檢察官起訴菅家先生而起。此處檢察官起訴菅家後的偵訊過程大有問題。
拿其中兩次分別是案發一年後1992年12月7日與隔天12月8日的偵訊錄音帶來當作例子。第一卷裡面,檢察官要菅家先生輕鬆的回答,說出實話沒關係,並且提了幾個關心他的問題,詢問他為何實情究竟是如何等等。菅家先生因為檢察官這樣的提問方式和開放式的問題而做出了真實的否認。但隔天檢察官像換了一個人似的,質問他說「昨天說沒犯案但其實不就是真的有做嗎?」、「犯人的精液和你的精液符合呢,你以為有幾個人會跟犯人一樣啊?」、「你為什麼不看著我的眼睛說話你在鬼扯對吧!」……連珠炮串式的質疑和封閉式的問句讓菅家先生又哭著自白坦承犯案。
由此可見,偵訊人員錯誤的確信會引出不實的自白,並且在封閉式問題的轟炸下,無辜的人也會輕易的自白犯案,冤錯就此發生。偵訊中應該建立的是開放式的對話,讓訊問者和嫌疑人彼此都有說話的空間,並且建立起兩人間的信賴關係,才能得到真實的自白,而非在認定他人有罪的前提下進行訊問,導致冤案產生。這是任何人都必須去深刻反省的,因為到目前為止,這樣的過錯仍反覆在發生,而這正是所謂足利事件的衝擊。
藉由DNA鑑定進行冤罪救援的意義
美國的無辜計畫累積了藉由DNA鑑定證明無罪的案例,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而從菅家先生的案子能看見正確的DNA鑑定可以還人清白,錯誤的DNA鑑定卻會錯害無辜。而無辜計畫顯示出的是,只要能做DNA鑑定,就較容易能夠證明有冤。
各國的刑事司法制度各有不同,同樣的證據在每個國家被採用的狀況不一定,但DNA鑑定不是如此,它普遍適用於各處,具有從根本改變司法判決的力量。DNA鑑定本來就是中立性的證據,現今卻仍普遍只用來作為有罪證據,這樣做是錯的。經由DNA鑑定而改判無罪的判決雖可能傷害國家威信,但從錯誤中學習而建立更完善的刑事司法制度才會是真正民主的刑事司法。
在法庭裡,被告方跟告訴方像是在互相對抗,但其實辯護人與檢察官或警察之間並非敵人(enemy)關係,他們更像是相互競爭、勢均力敵的對手(rival),必須要有好的對手,整體才能夠真正進步。
目前佐藤律師還承辦了另一件強制性交案的再審聲請,此案與足利事件幾乎同時期發生,而且也是因為科警研的鑑定使被告被當成犯人。好消息是,被害者沾有犯人精液的睡袍正被低溫保存著,最近法院要實施再鑑定,此可稱為第二個足利事件。佐藤律師期望有天能夠來台說明此案,並且他會繼續進行冤案救援,並盼望所有冤屈者都能夠平反,也盼望所有法律人員都能夠仔細的面對每一個案子,謹守基本的信念和法則,不要再誤他人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