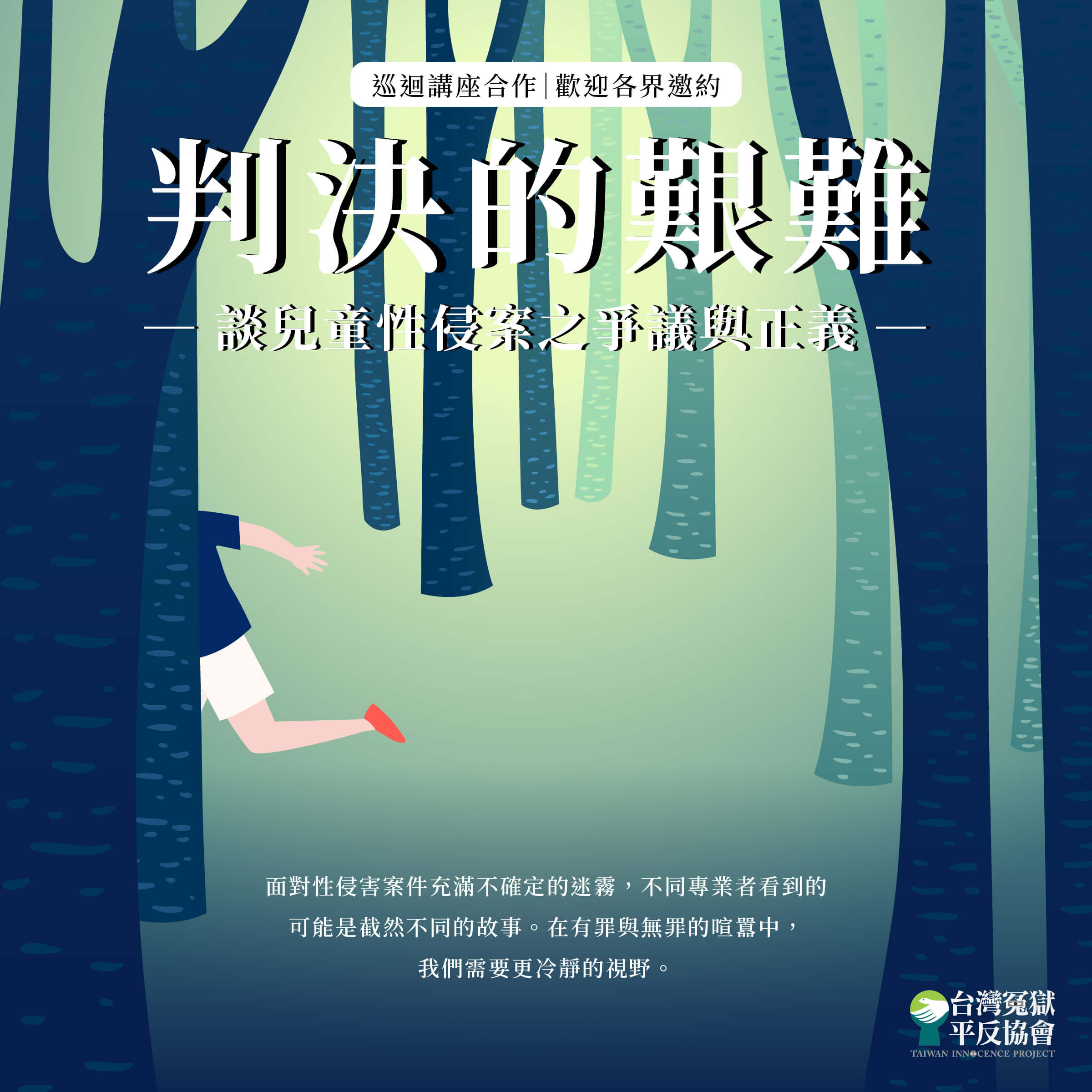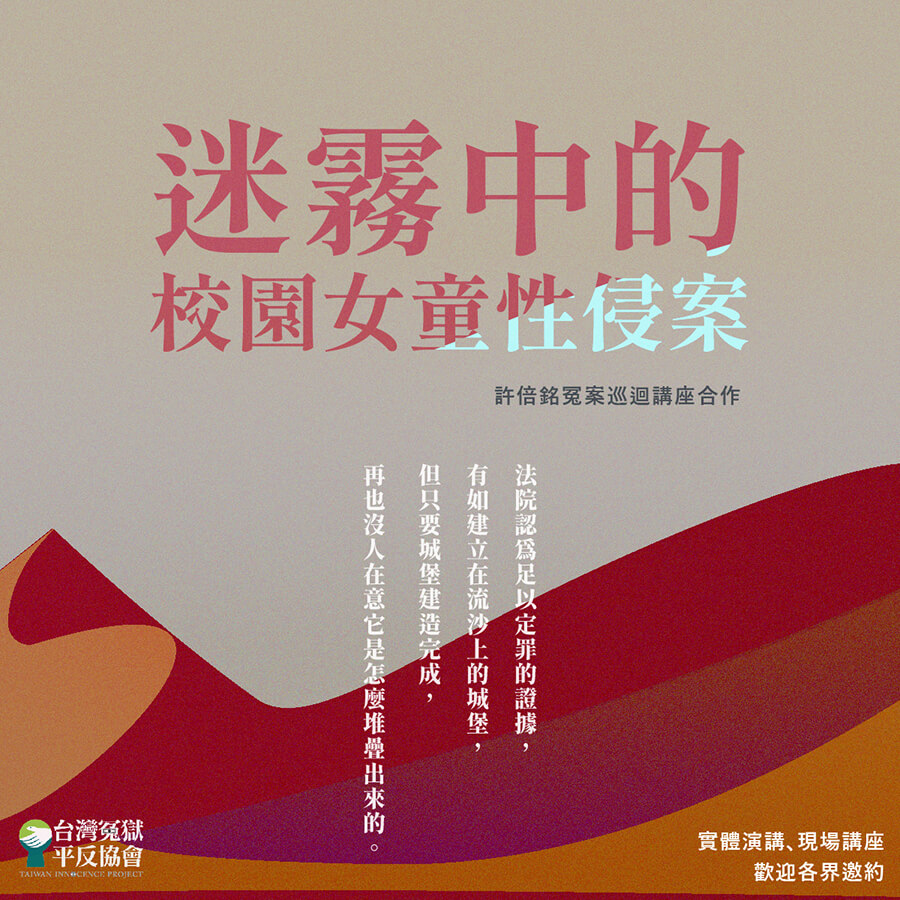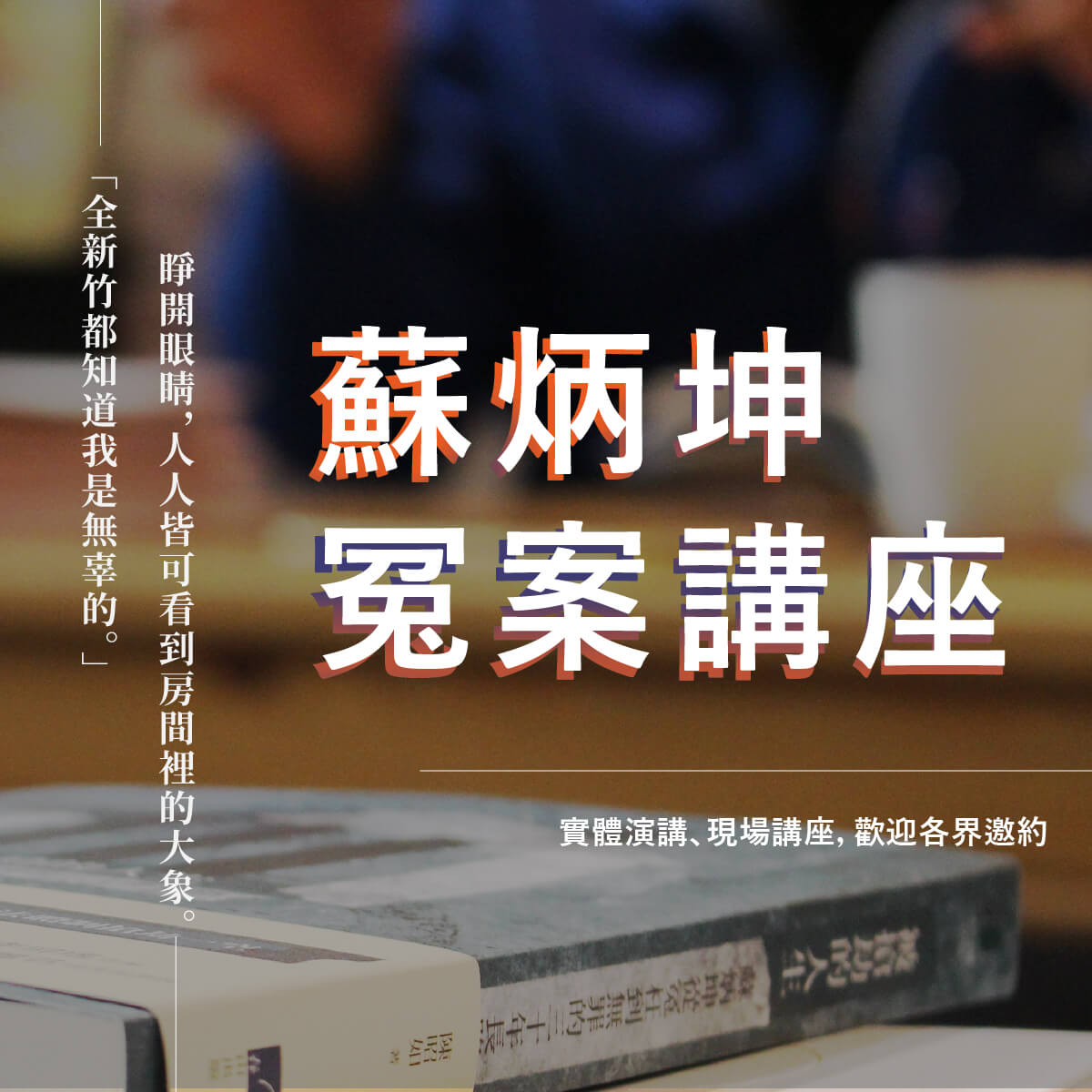冤案救援的場域,除了法庭內,還包括法庭外。我們相信,透過敘述、分享與聆聽,將能拉近社會大眾與冤案議題的距離,進一步促成改變的力量。
無論是想認識冤案救援工作、被冤者的冤案故事,還是想更了解司法出錯的原因及制度改革的可能性,我們都很願意用一場講座的時間與大家分享。歡迎各級校園、社團工會、機關組織與我們連繫,我們將視情形安排媒體工作者、冤案當事人、冤案救援律師或台灣冤獄平反協會工作人員共同擔任講師,帶領大家認識冤案、集結關心與支持的力量!
歷年主題講座
盧正冤案—《島國殺人紀事2:盧正案》紀錄片巡迴計畫
「也不是說我們有多大的力量,只是說讓社會的人知道更多,也許有可能你自己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現在我弟弟已經被槍決,我們不是在為我們自己做事情,我們希望往後的人,不要跟他一樣。」──盧菁、盧萍
2001年,蔡崇隆導演拍攝、製作了《島國殺人紀事2:盧正案》,記錄了盧正二位胞姊為盧正爭取清白,起身面對龐大國家機器的行動過程。本片製作完成至今已超過了二十三年,盧正尚未平反,正義尚未到來,紀錄片仍是進行式。
在過去一年間,我們總共完成了25場的《島國殺人紀事2:盧正案》紀錄片巡迴放映,搭配救援進度說明,細數幾大新證據,也說明平冤向監察院陳訴後所取得的新進展。2025年,紀錄片巡迴計畫將繼續滾動──我們希望帶著本片,到台灣各縣市的校園、電影院、影廳、咖啡店或其他公共空間播映,向更多人介紹盧正的故事,也讓社會上更多人知道盧正的冤情。
盧正還在等待,但行動刻不容緩。你的力量,也可能為案件帶來意想不到的進展。歡迎與我們聯繫,一起成為推動盧正案倡議行動的一員!
※ 協辦單位|公共電視台
判決的艱難—「談兒童性侵案之爭議與正義巡迴講座」
如何確認性侵案是否發生?向來是個難解的問題。
通常性侵案發生在密室,現場只有被害人與加害人,鮮少有直接的證據,就算被害人說得再聲嘶力竭,沒有客觀事實作為證據,不起訴或無罪的案例並不少見。這樣的判決邏輯常讓人感到困惑,明明被害是事實,為什麼一句「證據不足」就足以讓加害人全身而退,這公平嗎?
莫名其妙冤屈推擠著,成為無辜「加害人」的處境,又何嘗不是如此?如果因為沒有直接的證據,只有被害人的說法,執法者若因同情、貼近被害人而傾向相信被害人的說詞,這對無辜的被告來說,又公平嗎?
曾撰寫《沉默》、《沉默的島嶼》、《無罪的罪人》等校園性侵事件的陳昭如,在新作《判決的艱難》中,透過深度訪問被害人、無辜者、家屬、社工、律師、檢察官、法官等,剖析何以不同角色對「事實」的認定有不盡相同的看法,說明法院認定「證據」的標準是什麼,解釋「無罪推定」在司法程序中的意義與重要性;同時更指出一般鮮少提及的問題,那就是:被害人要的是什麼?法庭是否是他們追求正義的唯一場域?
事實上,無論是性侵被害人或是被冤枉的無辜者,都是視「性」為羞恥的文化之下的犧牲者。我們希望藉由與貴單位的合作,促成不同專業領域之間的對話與交流,共同構築更成熟承接性侵案件的司法制度,避免各種傷害擴大加深。
※ 講師|陳昭如
許倍銘冤案—「迷霧中的校園女童性侵案巡迴講座」
法院認為足以定罪的證據,都有如建立在流沙上的城堡,處處充斥著漏洞、矛盾與不連貫之處。但,就算這座城堡根本站不住腳,只要城堡建造完成了,再也沒人在意它是怎麼堆疊出來的。
——引自陳昭如《無罪的罪人-迷霧中的校園女童性侵案》
抱持著追尋正義的心,為何卻導致冤案發生?
2008年9月,許倍銘老師循著工作日常,替一名小學二年級的中度智能障礙同學進行智力測驗。事後,許老師竟遭被控對學童犯乘機性交罪,無端捲入冤案。
從兒童證人的訊問,到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之鑑定,本案中的每個角色,或因同情、或為正義,但這些情緒不但干擾了他們所做的判斷,也使得本案真相愈辯愈混亂。
多年下來,許倍銘始終喊冤,經親友家人奔走申冤,2016年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與台灣冤獄平反協會共同立案,展開法律救援;2019年作家陳昭如撰寫《無罪的罪人:迷霧中的校園女童性侵案》一書,並也開啟全台的巡迴講座,解讀許倍銘案的層層迷霧。
至今,許倍銘還在深夜中等待平反。
※ 講師|陳昭如
蘇炳坤冤案─「堅持清白32年,冤案平反者蘇炳坤案推廣計畫」
蘇炳坤說過:『全新竹都知道我是無辜的,只有法官不知道。』……這就像房間裡明明有隻大象,龐大到讓人無法否認、忽視它就在那兒,但就是沒有人談論,假裝它並不存在。」
——引自陳昭如《被搶劫的人生-蘇炳坤從冤枉到無罪的三十年長路》
沒有被冤枉過的人,無法瞭解清白有多麼重要。
即便已經總統特赦,並宣告罪刑全免,蘇炳坤仍希望司法體系能還他無罪與清白,讓他能獲得徹底平反。
儘管蘇炳坤在當年經徹夜刑求,仍堅持不妥協認罪。然而,蘇炳坤卻被認定與也受逼供的郭中雄,夥同犯下金瑞珍銀樓搶案。蘇炳坤用他人生中大把的歲月來為平反奮鬥。不過,即便已經三十個年頭過去,這個案件對蘇炳坤而言並沒有結束,他的人生已被這個案件給徹底改變,每每談起案情,蘇炳坤仍會不禁落淚。
「本院在此要對蘇先生你這段時間來所受的苦難,表達同情跟不捨,也希望蘇先生的苦難換來司法改革。」臺灣高等法院在無罪宣判時,法官對蘇炳坤說了這段話。
這對蘇炳坤、對社會而言,都具有莫大意義。遺忘是我們的習慣,但蘇炳坤所受的冤情,以及司法在這幾十年間的轉變,卻應該要被記得、被看見。